徵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台中南屯二代健保會計服務推薦最佳稅務後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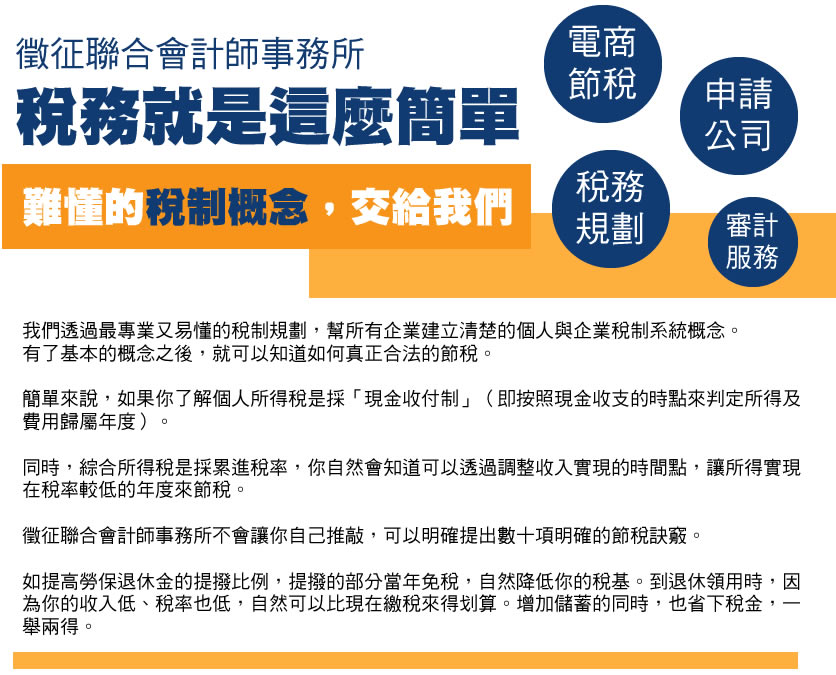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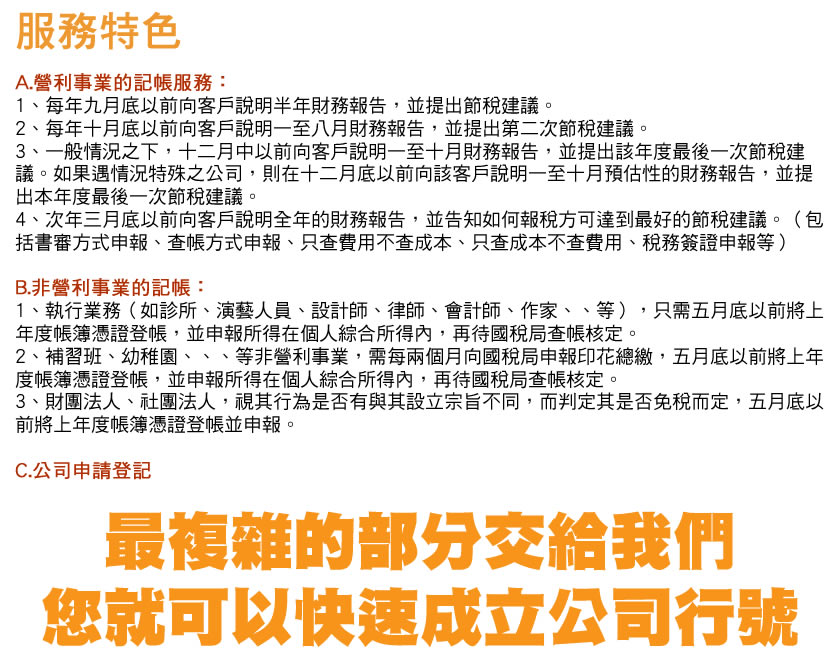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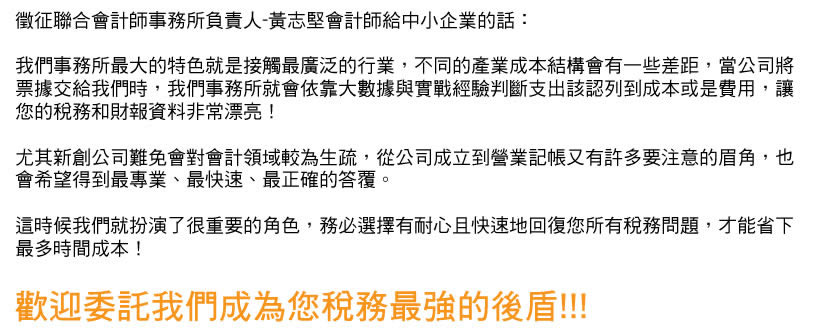
台中豐原精算諮詢會計服務推薦, 台中潭子企業會計準則稅務諮詢, 台中南屯家族企業審計會計服務推薦
巴金:一顆桃核的喜劇 《家》的法譯本序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后,有個朋友寫信問我,在按語中提到的沙俄皇位繼承人吃剩的一顆桃核的喜劇是怎么一回事。我現在來談一下。 首先讓我從《往事與隨想》中摘錄三段話來說明這件事情: 在一個小城里還舉行了招待會,皇位繼承人(皇太子)只吃了一個桃子,他把桃核扔在窗台上。官員中間有一個喝飽了酒的高個子馬上走出來,這是縣陪審官,一個出名的浪子。他從容地走到窗前,拿起桃核放進衣袋里去。 招待會之后,陪審官走到一位有名的太太面前,把殿下親口咬過的桃核送給她,太太很高興地收下了。然后他又到另一位太太那里,又到第三位太太那里——她們都十分歡喜。 陪審官買了五個桃子,取出了桃核,使得六位太太都非常滿意。哪一位太太拿到的桃核是真的?每一位都以為她那顆桃核是皇位繼承人留下來的…… 在“四害”橫行的日子里,這種“喜劇”是經常上演的。不過“皇位繼承人”給換上了“中央首長”,或者是林彪,或者是江青,甚至別人,桃核給換上了別的水果,或者其他的東西如草帽之類。當時的確有許多人把肉麻當有趣,甚至舉行儀式表示慶祝和效忠。這種丑態已經超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沙俄外省小城太太們的表演了。我們在某一兩部影片中還可以看到它的遺跡。除了這種“恩賜”之外,十多年來流行過的那一整套,今天看起來,都十分可笑,例如早請示、晚匯報、跳忠字舞、剪忠字花、敲鑼打鼓半夜游行等等、等等。 這些東西是從哪里一下子跳出來的?我當時實在想不通。但是后來明白了:它們都是從舊貨店里給找出來的。我們有的是封建社會的破爛貨,非常豐富!五四時期這個舊貨店給沖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給保護起來了。蔣介石后來又把它當做寶庫。林彪和“四人幫”更把它看做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四人幫”打起“左”的大旗,大吹批孔,其實他們道道地地在販賣舊貨。無怪乎林彪整天念他的“政變經”,江青整夜做呂后和武則天的夢。“四人幫”居然混了十年,而且越混越厲害,在國際上混到了個“激進派”的稱號。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想起來既可悲又痛心。 我常常這樣想:我們不能單怪林彪,單怪“四人幫”,我們也得責備自己!我們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貨色,林彪和“四人幫”販賣它們才會生意興隆。不然,怎么隨便一紙“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不然怎么在某一個時期我們會一天幾次高聲“敬祝”林彪和江青“身體永遠健康”呢? 在抗戰的八年中我常說自己“身經百炸”,沒有給炸死是僥幸。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常說自己“身經百斗”,沒有“含恨而死”,也是幸運。幾乎在每次批斗之后,都有人來找我,或者談話或者要我寫思想匯報,總之他們要我認罪,承認批斗我就是挽救我。我當然照辦,因為頭一兩次我的確相信別人所說,后來我看出批斗我的人是在演戲,我也照樣對付他們。在那種場合中我常常想起我小孩時期的見聞。我六七歲時候,我父親在四川廣元縣當縣官,我常常“參觀”他審案。我一聽見有人叫喊“(www.lz13.cn)大老爺坐堂!……”我就找個機會溜到二堂上去看。被告不肯講就挨打。“打小板子”是用細的竹板打光屁股。兩個差役拿著小板子左右兩邊打,“一五一十”地數著。打完了,還要把挨打的人拖起來給“大老爺”叩頭,或者自己說或者由差役代說“給大老爺謝恩”。 我當時和今天都是這樣看法:那些在批斗會上演戲的人,他們撈演的不過是“差役”一類的角色,雖然當時裝得威風凜凜仿佛大老爺的樣子。不能怪他們,他們的戲箱里就只有封建社會的衣服和道具。 封建毒素并不是林彪和“四人幫”帶來的,也不曾讓他們完全帶走。我們絕不能帶著封建流毒進入四個現代化的社會。我四十八年前寫了小說《家》。我后來自我批評說,我反封建反得不徹底。但是那些認為“反封建”已經過時的人,難道就反得徹底嗎? 沒有辦法,今天我們還必須大反封建。 二月十二日 巴金作品_巴金散文集 巴金:長夜 巴金:夢分頁:123
別怪世界不公平,是你還不夠強大 文/傅盛 去年年底,我獨自一人,從北京開車到廣州,一路三千多公里,都在思考一個問題:人和人的差別究竟在哪?人和人之間為什么會有差別?我想到了一個詞:拆掉思維的柵欄。 后來,我在機場看到了《拆掉思維的墻》這本書,心有戚戚。我一般不看成功學的書,事實上我也不認為這是一本成功學的書。作者的思考給了我很多啟發。我發現,有時候限制就是限制本身。你認為做不到,你就真的做不到。你覺得自己可以更強大,你就真的變得更強大。 你有沒有想過,真正限制我們的,是我們思維里看不見的墻?而這堵墻很大部分來自于內心的不安全感。我認為安全感的本質,不是你真的安全,而是你不害怕危險,敢于面對困難。記得有人問過我“上市后最大的收獲是什么?”我說,最大的收獲可能就是內心的所謂安全感,面對這個世界時,內心的想法沒有了那么多限制。 每個人心里都在追逐安全感。這很正常。但很多人成為了安全感的奴隸。什么是安全感的奴隸?就是害怕改變,保持現狀,聽他人的。追求安全感是人的本能,但安全感的獲得必須通過內心真正的強大。安全感是給予,不是索取。恐懼越多,索取越多,不安全感反而遞增。 正是因為很多人對于這個世界充滿了恐懼,生活中也有很多困難,我們很多人才不自覺的變成一種受害者,這就叫“受害者心理”。這種恐懼和不安全感,滋養了一種受害者心態。遇到困難的時候,你總會覺得世界不公平,充滿了各種問題。作者把這種模式歸結為受害者天堂。 什么叫受害者天堂?就是一個受害者最愿意去的地方。大家聚集在那,彼此安撫,然后覺得人生真是這樣。作者總結了受害者天堂的幾個法則。 “受害者天堂”法則一:推卸責任,保住面子 一切問題都不管我的事,不是我的錯。 如果一個孩子沒學好,父母問起來,受害者就會說,不是我不好好學,是老師講得不好;如果一個任務沒完成,卻受到上司的質問,受害者就會說,不是我的問題,這是客戶太變態。 受害者有一整套這樣的邏輯。不是我的問題,是別人不好;不是我的問題,是我小時候沒這個條件;不是我的問題,是這個社會太浮躁。在受害者天堂,大家從來沒犯過什么錯。美德都是他的,錯誤都是別人和社會的。 當然,他們也沒做成過任何事情。作者在書中提到,受害者也不需要成就什么,他們只要不斷的傾訴和編故事就好了。但問題在于,這個故事一開始很真實,后來慢慢就開始夸大,然后自己也慢慢相信——他生活在一個老板變態,老婆不可愛,老師不好的世界里。 很多同事向我抱怨自己有多難。其實那些所謂的“難”,在我面前根本就不用比。我們創業的時候多難呢?那個時候,因為要趕工作,我連爺爺最后一面都沒有見到。下了汽車之后,我都不敢回去,坐在路邊哭了好久。就在那種情況下,我每天還要打電話催促大家干活。 但是,每當我說到這兒時,他們還有一招。他們會說,你是老板,所以應該的啊。這就是蛋和雞的問題。難道我從第一天開始就是老板嗎?這又是個萬能的破解法。 總之,在受害者的天堂,一個人做不好事情,絕對不是個人能力的問題,而是這個事情有問題。 “受害者天堂”法則二:安心做壞事 在職場中,很多人每天不努力工作,也可以心安理得,為什么呢?因為他覺得,這個公司太爛了,這個老板太變態,太不理解我們,所以我這樣就OK了。 美國有一項研究,在辛辛監獄中,幾乎沒有哪個罪犯會承認自己是壞人。他們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辯護,他們都堅信自己不應該被關進監獄。很多做壞事的人都擁有一個完美的受害者的故事。 曾經,我當部門經理的時候,我會告訴組里的人,跟著我很苦,要是覺得不舒服就換一個機會。但只要你留在這里一天,就要對得起自己的每一天。別說對得起這家公司,首先對得起自己。還有什么比自己的時間更寶貴呢?所謂的為公司干,不就是為自己努力嗎?如果這個都想不通,還心安理得,就別一起干了。否則,不如自己找一個更舒服的環境。 事實上,這個世界根本沒有會讓你舒服得一塌糊涂的環境。必須自己不斷變得強大,去勇敢地面對這個世界。 “受害者天堂”法則三:分享凄慘故事會 受害者都有一個共同的嗜好,就是比慘。大家聚在一起分享各種凄慘故事,演變成凄慘故事會。 這種凄慘故事會,不只是存在于人們茶余飯后的談資,整個社會都變成了這樣。比如,每個電台都有一檔節目或好幾檔節目,都在講述誰比誰慘。在這種節目里,老婆必須出軌,男友一定不忠,兒子肯定不孝順。收視率還相當高。因為看過這些節目的人,都會找到安慰,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么慘的事情。 每個人都在別人的受害者故事中,獲得不少廉價的快樂和虛無的安慰。 作者在書中也舉了很多生動的例子。在受害者天堂,如果你失戀了,你的女伴會集體聚集過來陪你喝酒,說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難道他們都試過了?);如果你上午被老板罵了一頓,你會很快的被吸收進公司的受害小隊,他們中午聚餐的主要任務就是一起討論自己老板有多變態(我也不知道自己被討論過多少回了);如果小孩子不小心摔倒在地上,哇哇大哭,家長不會責怪小孩沒走好,會打地板說,地板錯錯錯,小孩子開心的笑了。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天堂里,居然浸泡其中,慢慢習慣,然后沉浸,開始分享。受害者天堂幫助“受害者”輕松獲得同情和幫助,就像一個人生病之后,就覺得可能有人會看望他一樣。他們在這個舒適的受害者天堂,陷入了無盡的情感黑洞。 但是,怎么辦呢?其實核心就是自己去掌控。首先要承認一個殘酷的現實——這個社會就是不那么公平。但這并不影響你在社會上快樂的工作。那么,如何才能從一個受害者變成一個掌控者呢? 你真的足夠強大嗎? 不妨先進入一種誠實的思考:不管什么情況,你都可以負全責。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做得更好,甚至可以做一種心理假設——如果把所有經歷過的事情重新倒退一遍,所有條件都不改變,只有自己改變,你能否做一個更好的結果呢?如果答案是Yes,那么你就開始進入掌控者的角色;如果你的答案是No,那你就是認為自己以前已經做的足夠好了,所有的不好都是別人的問題。 回想跟徐鳴創業的時候,我們兩人經常把自己鎖在辦公室里相互檢討,不斷反省哪件事情沒做好,哪件事情還可以更好,會不會有更好的選擇。我以前認為這是個好簡單的問題,后來跟很多人交流,發現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因為很少人愿意去面對否定的自己,那個過程很痛苦,需要不斷拋棄過去的自己。 以前總有人問我,經常有人攻擊你,你怎么辦?我說很好啊,沒關系。最能罵人的,把我都罵過一遍了,還有什么好怕的呢?盡管罵的時候很痛苦,但罵完以后,再回頭看,遇到任何這方面的事情,都不是問題了。 你所厭惡的八面玲瓏,你所憤恨的不公平 為什么上天對我這么不公平 別再抱怨上天了,這世界本來就不公平分頁:123
巴金:三次畫像 不久前畫家俞云階來看我,高興地告訴我,他的問題解決了。我也替他高興。我知道他說的“解決”不是指十一年中冤案的平反,不是指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這些應當早解決了,他的公民的權利,也早已恢復了。他講的是,給劃為“右派分子”的錯案現在得到了徹底的改正,是非終于弄清了。他摔掉了壓在頭頂上整整二十二年的磐石,可以昂起頭來左顧右盼,他當然感到輕松。他愉快地談他的計劃,他打算做不少的工作。我覺得他還有雄心壯志,他是一個一直往前看的人。 送走了這位畫家以后,我還在想他的事情。去年九月香港《文匯報》的《百花周刊》上發表了畫家的一篇短文《三次為巴金畫像》。他講的是事實,我和他之間的友誼是跟畫像分不開的。 我本來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有一天當時中國美術家協會上海分會的負責人賴少其同志對我說,要介紹一位畫家來給我畫像,我們約好了時間,到期俞云階同志就來了。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他。人似乎很老實,講話不多,沒有派頭或架子,有一種藝術家的氣質。我記得就在我樓下的客廳里,他花了四個半天吧,我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一點不覺得麻煩。油畫完成了,他簽了名送給我,我感謝他,把畫掛在我的工作室的墻壁上。說實話,我并不喜歡這幅畫像,但這不能怪畫家,我自己拿著書在打瞌睡嘛。對畫家本人,我倒有好感。 這是一九五五年十月的事。以后我似乎就沒有再看見畫家了,也不曾去找過他。反正運動一個接一個,不管你是什么家都得給卷了進去,誰還有時間去找不怎么相熟的人聊天呢!反右斗爭過后,我才聽說俞云階同志給戴上了右派帽子。我當時就覺得奇怪,他倒像一個不問政治的書呆子,怎么會向黨猖狂進攻呢?然而那個時候連我也不愿意做上鉤的“魚”,對俞云階同志的事情只好不聞不問,甚至忘記了他。日子就這樣過去了。 但是那幅油畫像還掛在我的工作室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我靠了邊、等待造反派來抄家的時候,我才把它取下,沒有讓造反派看見,因此它也給保存下來了。前年(一九七七)五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上海文藝界的座談會,在友誼電影院門口遇見畫家,我高興地同他握手,告訴他:“你二十二年前給我畫的像,現在還在我家里,好好的一點也沒有損壞!”這的確不是一件尋常的事。這十一年里我認識的人中間,哪一家不曾給造反派或紅衛兵抄家幾次?有關文化的東西哪一樣在“浩劫”中得到保全?我燒毀了我保存了四十年的我大哥的一百多封書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我大哥絕命書的抄本(這是我請我九妹代燒的),但是我竟然保全了這幅“反動權威”的“反動”畫像,連我自己也感到意外! 我老了。畫家也變了,他似乎胖了些,矮了些,也更像藝術家了。他親切地微笑道:“我再給你畫一次,好不好?” 座談會結束以后,畫家有一天到我家來做客,談起畫像的事,他說:“上次給你畫像,我還年輕,現在比較成熟了些,你也經受了這一次的考驗,讓我再給你畫一幅像,作個紀念。”我同意了。他又說:“在你這里干擾多,還是請你到我家里去,只要花半天時間就行了。”他還說:“你還是穿這件藍布上衣,連胡子也不要刮。” 我按照約定的時間到他的家。的確是一位油畫家的畫室。滿屋子都是他的畫,還有一些陳設,布置得使人感到舒適。我只坐了一個半小時,他的畫完成了。那天是六月四日,他說:“就寫五·二三吧。”過了一個星期畫家夫婦把油畫像給我送來了,我們把這幅新畫掛在我那間封閉了十年、兩個月前才開鎖的工作室的墻壁上。畫家看了看畫,還加上一句解釋:“你這是在五·二三座談會上控訴‘四人幫’的罪行。”我覺得他說得好。 這幅畫像在我家里已經掛了將近兩年,朋友們看見它,都說不像,說是臉長了些,人瘦了些。可是我喜歡它。我覺得它表現了我當時的精神狀態,我在控訴,我憤怒。我就是這樣。 但畫家似乎有不同的看法,過了幾個月他又來向我建議,要給我再畫一幅肖像,要把我“真實的熾烈的心情寫進畫面”①,要畫出一個煥發青春的老作家來。他的好意和熱情使我感動,我不便推辭,就答應了。其實我對一般人所謂“煥發了革命的青春”另有自己的看法。從去年四月七日起他帶著畫稿到我家里來。正如他自己所說,在我的工作室里“足足耗上了六個半天”。他相當緊張,真是付出了辛勤的勞動。 他的畫完成了,送到華東肖像畫展覽會去了。我向他道賀,可是我仍然說,我更喜歡那幅油畫頭像。我祝賀他成功地畫出了他的精神狀態,表現了他的“愉快”,他的“勤奮”,他的“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信心”。他畫的不一定就是我,更多的應當是他自己。我不過是畫家的題材,在畫面上活動的是畫家的雄心壯志,畫家對我們這個時代、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深厚感情。站在這幅畫前面,我感到精神振奮。畫家更成熟了,更勤奮了,對自己的藝術創作更有信心了。 兩年來我常常聽見人談起“煥發了革命的青春”,有時指我,更多的時候是指別人。拿我來說,我考慮了幾個月,我得到一個結論:我不是“煥發了青春”,也不是“老當益壯”。我只能說,自己還有相當旺盛的生命力,“四害”橫行的時期,我的生命力并未減弱、衰退,只是我不能工作,不得不在別的方面消耗它。那個時期,“四人幫”及其余黨千方百計不要我多活,我卻想盡方法要讓自己活下去。在這場我要活與不要我活的斗爭中,沒有旺盛的生命力是不行的。“四人幫”給粉碎以后,我的生命力可以轉移到別的方面,我可以從事正常的工作和寫作,我當然要毫無保留地使出我全身的力量,何況我現在面對著一個嚴酷的事實: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寫的作品全寫出來,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閉上眼睛,這是我最后的愿望(www.lz13.cn)。因此今天鼓舞我奮勇前進的不僅是當前的大好形勢,還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內傷。老實說,我不笑的時候比笑的時候更多。 那天云階同志走了以后,我關上大門,在院子里散步,還在想他的事情。我忽然想起王若望同志的一句話:“他生活困難到了不名一文的地步。”① 這是講云階同志那一段時期的生活的。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看來,他真堅強。兩年來同他的接觸中我一直沒有感覺到一九五七年給他投下的陰影,我始終把第三次肖像畫上的笑容看做他自己衷心愉快的歡笑。現在一句話說出了畫家二十二年中間悲慘的遭遇和所受到的種種歧視。“右派分子!”“摘帽右派!”將來不會再有什么“改正了的錯劃右派”這頂帽子吧。那么這樣一位有才華的藝術家所身受的種種不公平的待遇也應當從此結束了。 三月十七日 巴金作品_巴金散文集 巴金:蘇堤 巴金:長夜分頁:123
ACC711CEV55C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